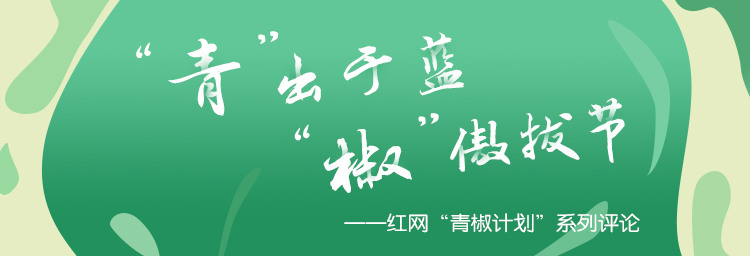这些天“贾浅浅”因部分诗歌里的“尸字头”的描绘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除了“贾浅浅”和他的父亲,除了持续发酵的网络舆情,我们还须关注到新诗生态的本身,毕竟,分不清是对人对事还是对诗的网络批判,难以掬一抔诗的倒影。
《诗·大序》这样评价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简单地说,就是“诗言志”,它是情智的外显。为着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五四时期在文化自觉的召唤下白话文逐渐代替文言文,诗歌也逐渐要打破旧诗词格律的桎梏,追求诗体的解放。
自此,新诗与传统格律诗此起彼伏连缀出宏大的中国诗境。
艾青认识到,“自由体的诗带有世界性的倾向”,这点有目共睹。但现在新诗创作也出现了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部分创作者还是会模糊新诗与古诗的创作,最终不伦不类。新诗诞生发展到现在,甚而出现了极端:“生活是写作的源泉”,部分诗词创作者大抵是误解了这“三分文学,七分生活”的道理,将生活里口语化的词汇不加选择地排列在一起;误解了郭沫若所说的“‘不定型’正是自由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把一句正经的话,多加几个逗号,就像结巴一样,回行表达出来,就成了诗;又或许是受俄国形式主义诗学“陌生化”理念的影响深了,相当一部分的新诗创作很懂得包装,把白话表达得难懂,把“简单”处理成复杂,越突破常情常理越晦涩。
关于新诗的争论,关于新诗的标准界定,不是一天两天了。诸如“贾浅浅”此类能令人为着诗、为着诗歌、为着诗性争一争的现象,近几年其实是冒出了一茬又一茬。可或许,那些新诗创作者还不够“贾浅浅”,不够引发网络舆情,也就未得到广泛关注。
贾浅浅――贾平凹之女,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当代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参加第35届青春诗会,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诗刊》《作家》《十月》《钟山》《星星》《山花》等,出版诗集《第一百个夜晚》《行走的海》,出席第八次全国青创会,荣获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
因“文二代”的标签,因身上担着这一系列的文学头衔,“贾浅浅”这三个字,显然更容易被借势制造舆论,博得眼球。怕的是,这只是一场借“热”炒“热”,而后,沉默的继续沉默,恶搞的继续恶搞,溜须怕马的继续溜须拍马。
“贾浅浅”的诗歌写得好与不好,众说纷纭,暂无定论;但关于诗歌创作本身的好与不好,确实不能再睁眼说瞎话,该实事求是了。很多时候,面对不入流的“大咖大作”到底掺了多少水分,所谓“大家”“大师们”是心知肚明。可非但没有争议,反而充斥吹嘘赞美。那么,“普通人”就更是不敢直抒胸臆地评价,只能随大流接收与接受了。
越来越多的人,涌进诗词创作的世界狂欢,越来越多连基本的诗歌常识都不懂却顶着“诗人”光环的人,热衷于写下各种“打油诗”“梨花体诗歌”发表出版,于是我们也就看到了大量用现代语汇嵌套古典诗词格律的仿古文学作品,看到了某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某晚报上发表“纵做鬼也幸福”这灾难文艺出现的不合时宜。
可若当文学工作者都不再沉心静气,难以潜心于他的创作耕耘,更在乎追逐知名度、曝光率了,当各地作家协会会员未深入于诗词研究却惯以“指点江山”故弄玄虚了,当文学批评的评价维度不是就作品而论作品,而是更顾虑于人脉关系与金钱利益了,当读者跟随流量先关注到“贾浅浅”,才留意到新诗生存的境况本身,唇枪舌剑、口诛笔伐下忽略“文学就是人学”的要义了,那即是“诗言志”都尚且难以确保做到,又何谈伸张“诗性正义”?
文/谭成艳(重庆交通大学)
来源:红网
作者:谭成艳
编辑:张瑜
本文为红辣椒评论原创文章,仅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红网立场。转载请附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