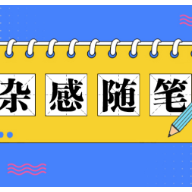□戴若冰
在我们家里,管大嫂叫嫂嫂。嫂嫂是什么时候嫁给大哥的呢?曾经问过母亲,母亲瞪我一眼,嗔道:“小娃儿莫管闲事!”
后来才知道,嫂嫂是五岁时就来到我们家的。那时是旧社会,嫂嫂的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孤儿寡母,生活无着落,嫂嫂的母亲带着她讨口叫化。我的母亲便把前来要饭的嫂嫂收留下来,做了大哥的“童养媳”。
我的母亲也是苦命人,父亲去世那年,我最小的弟弟还在襁褓里。家里“顶梁柱”走了,“长哥为父,长嫂为母”,大哥大嫂自然成了母亲的左膀右臂。
大哥学了一门烧砖瓦的手艺,隔三差五外出烧砖瓦,挣点钱补贴家用。二哥小学没毕业就跟着小舅学木匠去了。于是,我们这个七口之家,就只有嫂嫂和母亲挣工分。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年代,社员们集体出工,各家各户凭工分计酬分粮食。
有一年初夏,秧苗栽下去,久旱不雨,很多稻田都需要戽水灌溉。为了多挣些工分,嫂嫂向队长申请,承包了十几亩稻田的浇灌任务。白天,嫂嫂和母亲照样出工;晚上,趁着月光,她和母亲戽水灌田。我便负责看水,光着脚板,挽起裤腿,一块田一块田地查看,待灌满一块田,再灌另一块田。
有个晚上,由于时间不早了,第二天我要上学,母亲便叫我带着弟弟回家睡觉,弟弟赖着不肯回家。结果,他在草坪上睡着了,梦见家里蒸了一大锅白米干饭。
“吃新米饭时,嫂嫂会不会给我盛个冒儿头?”弟弟问我。在我老家,人们把满满一碗白米干饭叫做冒儿头。
“会的,一定会。”我安慰他。那年月,新米出来后,再穷的人家也要做一顿干饭尝新。
尽管母亲和嫂嫂拼命干活儿,但挣的工分还是比别的人家少许多。秋收后,别的七口之家可以分得十二三担谷子;我们家呢,只能分得七八担。所以,我们家常常过完大年,有时甚至不到过年,粮食就吃光了,只好到处借粮食,是村里名副其实的“漏斗户”。
我读四年级时,大哥在外面生了病,很久没寄钱回家了。一天,母亲去二孃家借粮食没回来。晚上,我们找不到吃的,嫂嫂喊我们早点儿睡觉,弟弟饿得哭,不肯去睡。嫂嫂一会儿掏掏这个坛坛,一会儿摸摸那个罐罐,都空空如也。只见她从堂屋踱进灶屋,又从灶屋踱进堂屋,后来打开大门,立在院坝里发呆。
夜,黑沉沉的,房前屋后,没有鸟鸣,没有虫叫,寂静得有些怕人。
母亲借到粮食了吗?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我正这么想着,突然嫂嫂对我说:“山凹,你去哄弟弟睡吧,我去接妈妈。”
可嫂嫂出去半天没回来。原来,她没有去接母亲,她摸黑去屋后的地里刨了几根红苕,被守夜的人抓住了。守夜人喊来队长,队长收缴了嫂嫂手里的红苕不说,还连夜召集社员开会,让嫂嫂作检讨。会上,嫂嫂低着头,咬紧嘴唇,始终没开腔。
偷刨集体的红苕肯定是不对的,但若因此否定嫂嫂的品格也不恰当,因为,嫂嫂并不是个爱贪便宜的人。更何况第二年春上,嫂嫂做了许多人难以置信的一件事:那天,她把分得的二十斤黑龙江苞谷背回家来,用秤再称一下,结果发现多了1斤,她连忙把多出的1斤苞谷送回保管室,交给了队长。
改革开放后,大哥开了打米加工厂,还开了个小卖部,嫂嫂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人至耄耋,她还能种瓜种菜,喂鸡养鸭,赶场买卖。嫂嫂最喜欢去吃镇上电影院楼下那家肯德基。
2020年冬天,嫂嫂去世了。我至今没弄明白,在那个靠黑龙江苞谷救济的年辰,她把多出的1斤玉米退还给队里,是不是想给偷刨那几根红苕的错误行为“赎罪”呢?没人知道,母亲也从不提起。我只记得母亲生前说过,嫂嫂勤劳、善良、忠厚、老实,是个好媳妇。
来源:红网
作者:戴若冰
编辑:张瑜
本文为红辣椒评论原创文章,仅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红网立场。转载请附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